方立天:慧远的政教离即论
2025-04-07 11:5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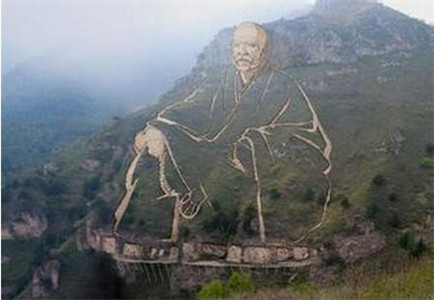
内容提要:慧远提出政教离即论,系统阐发了佛教与政治既相离又相即的主张。他十分强调出家僧侣独立于政治,强调政教分离,同时又多方面论证佛教与政治的一致性,肯定其相即不离的关系。从总体来看,佛教既独立于政治,又有益于政治的观点,是慧远政教关系思想的出发点和归宿点。
佛教与中国封建中央集权专制王朝的关系,既有适应协调的一面,也有矛盾冲突的一面。如何处理与封建专制王朝的关系,是中国佛教必须面对的一个重要的理论问题和实际问题。东晋以来,以庐山东林寺慧远为首的佛教界人士与当时以桓玄为代表的政界人士,就沙门是否应当向王侯礼敬的问题展开了激烈的辩论,实际上就是关于佛教与政治的关系问题的辩论。慧远在辩论中撰写了《沙门不敬王者论》等论文,提出了政教离即论,系统地阐发了佛教与政治既相离又相即的主张。回顾这一段历史,考察当时引发论辩的历史背景,总结慧远的政教关系论说,对于我们了解历史上佛教与政治的关系、中国佛教的政治观,以及中国佛教的特殊品格,都是极有意义的。
沙门应否礼敬王侯的问题,早在慧远前半个多世纪就有庾冰与何充的辩论。东晋咸康六年(340),成帝年幼,政治家庾冰代执朝政, 竭力主张沙门见了皇帝应行跪拜礼。他在《代晋成帝沙门不应尽敬诏》(不字是衍文,下同)中说:因父子之敬,建君臣之序。名教有由来,百代所不废。⑴在《重代晋成帝沙门不应尽敬诏》(不字是衍文,下同)中又重申:礼重矣,敬大矣,为治之纲尽于此矣。王教不得不一,二之则乱。⑵意思是说,君臣父子的纲常名教,是治国的大纲,封建礼制由来久远,历百代而不废,今若尊卑不分,君臣失序,王教不一,国家必将大乱。庾冰在《代晋成帝沙门不应尽敬诏》中抨击佛教是矫形骸,违常务,易礼典,弃名教,⑶是方外之事为方内所体,是殊俗参治,怪诞杂化。⑷他认为在封建中央专制国家范围内,听任自居于世外的佛教僧侣易弃世俗礼教,以佛教习俗影响世俗政治是决不可取的,也是不能容许的。
当时的尚书令何充、仆射褚翌、诸葛恢等大臣对庾冰的主张则持有异议。他们在《沙门不应尽敬表》中充分肯定了佛教有益于王化的正面作用:寻其遗文,钻其要旨,五戒之禁,实助王化。⑸在《重奏沙门不应尽敬表》中也说:因其所利而惠之,使贤愚莫敢不用情,则上有天覆地载之施,下有守一修善之人。⑹并从历史的角度指出:直以汉魏逮晋,不闻异议,尊卑宪章,无或暂亏也。⑺认为事实上,自汉魏直至晋代的漫长时间里,并没有因佛教的流传而使纲常名教遭到破坏。
从庾冰和何充等人的对立观点来看,他们都是站在封建国家整体利益的立场,以封建纲常名教为参照系,来衡量佛教及其礼仪对整个封建统治的得失利弊。所不同的是,双方对佛教社会功能所作的价值判断大相迳庭。庾冰看到了佛教与封建集权、纲常名教的矛盾方面乃至不利方面,而何充等人则着眼于佛教与封建王权、纲常名教的统一方面乃至有利方面。这就鲜明而深刻地昭示人们,佛教与封建政治具有两重性关系,既有统一的正面作用,又有矛盾的负面作用,如何恰当处理和协调这两重关系,对封建统治者和佛教领袖来说,都是一个极其复杂而带有挑战性的历史课题。庾冰和何充等人是第一次公开在统治集团内部就佛教与封建政治伦理关系展开争论的,后经礼官、博士的评议与反复辩论,庾冰的主张没能实行,实际上等于宣告失败。
东晋末年,由于一些僧人干预政治的角色错位,以及与民争利等污浊流俗的泛滥,又引起政界的强烈不满。如比丘尼支妙音深得晋孝武帝和会稽王道子的敬奉。太元十年(385)道子为她建简静寺,以音为寺主,徒众百余人。内外才义者, 因之以自达。供@⑴无穷,富倾都邑。贵贱宗事,门有车马,日百余乘。⑻支妙音窃弄大权,结纳后妃,以至达到权倾一朝,威行内外⑼的显赫地步。当时中书令王国宝和桓玄都凭借妙音的特殊地位,请求妙音在孝武帝以及后妃面前为自己美言,以达到抬高声望,或晋升官位的目的。妙音的染指政治,使晋王朝更加失政不纲。这样,到了义熙年间,时人对僧人的指斥益发激烈、痛切,如说:
今观诸法门,通非其才,群居猥杂,未见秀异,混若泾渭浑波,泯若薰莸同箧。触事蔑然,无一可采。何其栖托高远,而业尚鄙近!至于营求汲汲,无暂宁息。或垦殖田圃,与农夫齐流;或商旅博易,与众人竞利;或矜恃医道,轻作寒暑;或机巧异端,以济生业;或占相孤虚,妄论凶吉;或诡道假权,要射时意;或娶畜委积,颐养有余;或指掌空谈,坐食百姓。斯皆德不称服,行多违法。虽暂有一善,亦何足以标高胜之美哉!自可废之,以一风俗,此皆无益于时政,有损于治道,是执法者之所深疾,有国者之所大患。⑽薰,香草。莸,臭草。薰莸,比喻善人和恶人。博易,贸易。寒暑两种病因。这段话指出,佛门并非自诩的那样纯净,而是良莠不分,鱼龙混杂之地。有的从事农、商与人争利;有的乱行医道,贻误病人;有的占卜看相,妄论凶吉;有的聚敛钱财,中饱私囊;还有的巧取权力,干预政治,这一切都被认为是有损于治国之道的大患。这些现象成为当时人们议论的热门话题,更成为一些对佛教持有异议的政治官员整肃佛教的口实。在这种背景下,沙门是否应敬王者的辩论又重新爆发了,并且由王朝内部的争论发展为以慧远为代表的佛教界与以桓玄为代表的封建王权之间的直接交锋。
桓玄站在儒家、道家的思想立场上,不仅反对佛教的因果报应论说,反对人们出家修道,乖离事务,还反对佛教僧侣遗礼废敬。桓玄总结庾冰和何充等人关于沙门应否礼敬王者争论时说:何、庾虽已论之,而并率所见未是,以理屈也。庾意在尊主,而理据未尽;何出于偏信,遂沦名体。⑾名体,名教。他认为何充、庾冰二人各有不足之处。何充偏信佛教,遂使佛教沦丧,而庾冰虽在尊崇、维护尊主,但理据又不够充分。他从理论上为沙门应尽敬王者又作了进一步的论证:
夫佛之为化,虽诞以茫浩,推于视听之外,然以敬为本,此处不异。盖所期者殊,非敬恭宜废也。《老子》同王侯于三大,⑿原其所重,皆在资生通运,岂独以圣人在位,而比称二仪哉?将以天地之大德曰生,通生理物,存乎王者,敬尊其神器,而礼实惟隆,岂是虚相崇重,义存君御而已哉?沙门之所以生生资存,亦日用于理命,岂有受其德而遗其礼,沾其惠而废其敬哉?⒀。三大,指道大、天大、地大。老子认为连同王者大,称为域中四大。⒁二仪,指天地。神器,帝位。桓玄认为,佛教的教化虽富超越感官的神秘性,但也是以敬恭为根本,这一点和礼教是一致的,并不是主张废除敬恭,只是佛教所追求的理想有所不同。《老子》一书把王侯与道大、天大、地大三大并列,同为宇宙间四大之一。王侯之所以在宇宙间有如此重要的地位,并不是因为王侯掌握着国家权力,地位崇高,而是说王侯和天地一样,都具有资生万物成长的大德,由此也就理所当然地应当与天、地一样受到人们的尊敬。沙门之所以得到生长存养也是有赖于王侯的德惠,难道有受王侯的德惠而又对他不礼敬的道理吗?桓玄从对人类和万物生存作用的视角出发立论,确立天、地、王侯同是应当受世人崇敬的对象,从而为沙门也应礼敬王者提供了哲学思想论据。
针对桓玄的议论,慧远在《沙门不敬王者论》和《答桓太尉书》中从多种角度阐明了沙门不应礼敬王者的理由,予以明确的回应。
首先,慧远把在家的信徒与出家信徒加以区别,肯定在家信徒必须顺应世俗礼法,尊亲敬君。他说:佛经所明,凡有二科:一者处俗弘教,二者出家修道。处俗则奉上之礼、尊亲之敬,忠孝之义表于经文,在三之训彰于圣典,斯与王制同命有若符契。⒂对于在家信徒为什么一定要礼敬王者,他又进一步阐明了个中原因:在家奉法,则是顺化之民,情未变俗,迹同方内,故有天属之爱,奉主之礼。礼敬有本,遂因之而成教。⒃慧远认为,在家信徒之所以有自然天成的对王者之尊敬,对父母之亲爱,关键在于他们情未变俗,迹同方内,就是说,他们居住在世俗人群之中,日常生活与俗人没有根本的区别,他们自然应当顺从世俗的教化,礼敬王侯,孝顺双亲。
然而,出家僧侣则完全不同。慧远说:出家则是方外之宾,迹绝于物。其为教也,达累患于有身,不存身以息患,知生生于禀化,不顺化以求宗。求宗不由于顺化,故不重运通之资;息患不由于存身,故不贵厚生之益。此理之与世乖,道之与俗反者也。⒄化,运化,自然变化。不顺化,不顺应变化。宗,宗本,宗极,终极理想。求宗,追求终极理想。在慧远看来,出家僧侣是世外之人,其行迹是超绝于世俗的。他认为,人身是一切烦恼和痛苦的根源与载体,只有形体消亡,才有可能彻底摆脱烦恼和痛苦。而人体的形成正是由于有生,人身生生不绝又是由于禀受阴阳二气的变化。因此出家人要反其道而行之,即不顺应自然变化,不重视生存,而要求宗,即追求终极理想,追求超越生死变化,达到永恒不变的涅pn@⑵境界。既然如此,桓玄所说的天、地、王侯对人类的资生之恩惠,对出家僧侣来说就毫无意义了。慧远又说:天地虽以生生为大而未能令生者不死;王侯虽以存存为功,而未能令存者无患。生生之大、存存之功,既不能使人们长寿永存,又不能消除痛苦患累。斯沙门之所以抗礼万乘,高尚其事,不爵王侯而沾其惠也。⒅慧远站在佛教出世的立场上,直面佛教与世俗社会、政治王权的矛盾,以沙门的最高人生理想驳斥沙门应恭敬王者的观点,表现出与封建王权相对抗的独立人格和无畏精神。
根据以上的理由,慧远进一步说:凡在出家,皆隐居以求其志,变俗以达其道。变俗服章不得与世典同礼,隐居,则宜高尚其迹。⒆他认为出家僧侣的处世特点,一是要隐居,二是要变俗。所谓变俗,就是不随俗,不顺化。诸如服饰鞋袜等方面都与世俗的典制不同。隐居,是为追求佛教理想而远离世俗,特立独行,高尚其行迹。这是慧远为出家僧侣所作的角色定位。在慧远看来,既然僧人要变俗,就不能结交朝廷,参与政治,屈服王朝,服首称臣,当然也不能与俗人、在家信徒一样礼敬王者。从中国社会发展史和中国佛教发展史来看,应当说,慧远的政教分离主张是合乎理性而有积极意义的。它有助于避免因僧人染指政治而使朝政不纲、政治腐败现象的出现,也有助于减少或避免王朝因运用政治力量和行政手段压制宗教现象的发生。
其次,慧远又从出家僧侣的社会作用角度,阐明佛教不仅在实质上不违背封建的纲常名教,而且对协助王权,庇护人民还有很大的益处。他说:夫然,故能拯溺俗⒇于沉流,拔幽根于重劫,远通三乘之津。广开人天之路。是故内乖天属之重,而不违其孝,外阙奉主之恭而不失其敬。(21)慧远认为,佛教具有化导世俗的作用,它引导人们超越现实社会和现实人生,通过不断超越,不断提升,以至最终获得佛果,成就人生最高理想人格。尽管从形式上看来,出家僧侣对父母没有尽孝,有失天性,对君主不恭,有失礼敬,但从实质上看,却不违背孝道,也不失却恭敬。慧远还进一步说:如令一夫全德,则道洽六亲,泽流天下,虽不处王侯之位,固已协契皇极,大庇生民矣。如此,岂坐受其德,虚沾其惠,与夫尸禄之贤同其素餐者哉?(22)一夫,此指沙门。六亲,指父、母、兄弟、妻、子。皇极,此指政治贤明。尸禄,居位食禄而不尽职。素餐,不劳而食。慧远在此进一步强调出家僧侣的社会政治作用,认为只要沙门出家勤于修持,道德高尚,成就了佛教功德,就能使自己的六亲乃至天下都得到好处,从而完全符合王侯的政治统治。由于沙门对社会的有益作用,就与那些尸禄素餐者完全不可同日而语。这里,慧远是以僧侣的宗教实践作用来论证佛教及其礼仪与封建礼仪不仅是相一致的,而且还有利于封建政治,进而证明沙门求宗不顺化思想是完全正确的,当然,沙门不敬王者也就没有什么大逆不道可言了。
再次,慧远还以世俗人们认识的局限性来肯定方外世界的存在,以进一步证明求宗的正确性。
当时尊崇儒家反对佛教的人认为,只有天最为崇高,只有唐尧能学习天。至于视听以外的事,都是子虚乌有,不可相信的。佛教讲的世外道理,追求的宗教是难以验证,不能成立的。(23)这种看法关系到慧远追求的终极目标是否真实可信,也即是否真能成佛,真有佛国世界的大问题,同时也关系到沙门不礼敬王侯而只崇拜佛陀是否合理的大问题。
慧远针对这个问题,明确地指出,佛教的神道世界,是人们的日常经验,一般认识所不能理解的。他说:夫幽宗旷邈,神道精微,可以理寻,难以事诘。虽应世之见,优劣万差,至于曲成在用,感即民心而通其分,分至则止其智之所不知,而不关其外者也。若然,则非体极者之所不兼,兼之者不可并御耳。(24)分,分限。这是说,佛国世界旷远精微,只能用佛理去探索,而难以用事实经验去诘究。虽然适应教化世俗众生的种种见解,有优劣的区分,至于因良好见解而有所受用的人,也只是达到认识的一定分限,超过这种认识分限则是人们的智慧所不能达到的,人们并不能认识方外世界。由此也可见,不是体悟宗极的成道者不了解世俗社会,不兼化众生,而是成道者难以统御众生,使之在世俗经验范围内体悟佛国世界。慧远以人类认识的有限性来肯定佛国世界的存在,进而证明沙门超越世俗社会以求宗的正确性,证明沙门不礼敬王侯的正当性。
附带地说,当时和慧远站在一边反对沙门应敬王者的也有重要官员,其中比较突出的是中军将军尚书令桓谦和领军将军吏部尚书中书令王谧。桓谦在他的《答桓玄论沙门敬事书》中说:视听之外,或别有理。令便使其致恭,恐应革者多,非惟拜起。又,王者奉法出于敬,信其理而变其仪,复是情所未了。即而容之,乃是在宥之弘。(25)认为视听之外和视听之内的理是不同的,人们不能否定视听之外的理的存在,也就不应该改革佛教的礼仪。如果要改革的话,象沙门不敬王者这样的事,要改革的还很多,一改再改,沙门也就不成其为沙门了。王谧和桓玄有多次书信往来,讨论沙门应否敬王者的问题。(26)王谧反对沙门礼敬王者的理由,主要有:一是沙门超俗出世,已经不是王侯的臣民了,不宜再要求他们履行世俗的礼法,礼敬王侯。二是从历史的角度看,外国的君主无不对沙门行礼;佛教在中国流行四百多年,历经汉、魏、晋三个朝代,一直不礼敬王者,也无害于社会秩序。由此可见,桓谦和王谧反对沙门应敬王者的理由与慧远的有关论证是一致的,立场也是鲜明的。
桓玄是慧远时的反佛先锋和主将,他反复强调说讨论沙门礼敬王侯的问题是一代大事,但在他篡位以后,又下《许沙门不致礼诏》,称:佛法宏诞,所不能了,推其笃至之情,故宁与其敬耳。今事既在已,苟所不了,且当宁从其略,诸人勿复使礼也。(27)桓玄放弃了要求沙门礼敬王侯的主张,大概不仅和佛法宏诞有关,也和慧远的竭力抗争有关吧!
值得我们注意的是,上面慧远关于求宗不顺化,反对沙门礼敬王者的论述,实质上是在阐述佛教与政治、佛教神权与封建王权的关系问题。慧远主张佛教与政治既应互相独立、分离,又应互相配合、协调一致,这种观点可以称之为政教离即论。
佛教传入中国以后,就外部环境来讲,它在中国的发展主要是受到了封建专制王权的制约。如何处理与封建政治的关系,实在是关系到佛教生死存亡的头等大事。从慧远以前的佛教情况来看,一些重要的佛教僧侣都是和政治保持联系的,都是在取得当政者支持的情况下推动了佛教的发展。例如慧远的师父释道安总结佛教与政治的关系说:不依国主,则法事难立,(28)强调佛教的生存和发展都必须依靠国主,必须与政治保持密切的联系。道安的师父佛图澄是后赵时代的重要佛教活动家,又是后赵政权的军政顾问,王朝有事必谘而后行,备受推崇和重用。佛图澄可以说是把传播佛教和参与政治有效地结合起来的一个典型。但是佛教僧侣卷入政治旋涡也会产生许多流弊,如上所述妙音染指政治就引起东晋王朝的动荡、混乱以及朝野一些人的强烈反对。
与热衷于依附、参与政治的僧侣不同,慧远竭力保持僧侣的人格尊严,高扬佛教的主体意识,维护佛教的独立地位。他影不出山,迹不入俗;他与朝臣进行辩论,为佛教作辩护;他建立庐山僧团,严谨修道,被视为道德所居,成为教团的样板。慧远正是以他离开政治的佛教实践而赢得了崇高的威望。他德高望重,砥柱中流,深为教内外人士所翕服,以至有震主之威的桓玄也不能不对他另眼相看。慧远为保持佛教独立于政治,为实行政教分离提供了成功的历史范例。
同样十分高明的是,慧远在坚持沙门不敬王者的同时,又着重强调了出家沙门的客观政治作用,认为沙门修道非常有利于王侯的政治统治,有利于稳定政治秩序,把沙门修道与王侯的政治利益联系了起来,也就是说,慧远认为沙门是通过出家修道的形式来为现实政治提供了帮助,从而肯定了佛教与政治相即不离的关系。慧远的这种说法确实有其合乎实际的一面,确能打动一些聪明的政治家的心灵,使其开窍,使其折服。
慧远强调在家的佛教信徒必须遵守社会礼法,孝亲忠君,也就是必须服从现实的政治伦理,不得违反。这是从大量的在家信徒方面肯定佛教与政治不能分离,确立了佛教与政治的相即不离的关系。
慧远在《沙门不敬王者论?体极不兼应》中讲到的体悟终极境界有先合后乖和先乖后合两种理论和方法,实际上也包含了慧远对佛教与政治关系的看法。慧远说:理或有先合而后乖,有先乖而后合。先合而后乖者,诸佛如来,则其人也。先乖而后合者,历代君王,未体极之主,斯其流也。何以明之?经云:佛有自然神妙之法,化物以权,广随所入,或为灵仙转轮圣帝,或为卿相、国师、道士。若此之伦,在所变现,诸王君子,莫知为谁。此所谓合而后乖者也。或有始创大业,而功化未就,迹有参差,故所受不同,或斯功于身后,或显应于当年,圣王则之而成教者,亦不可称算,虽抑引无方,必归途有会,此所谓乖而后合者也。若令乖而后合,则拟步通途者,必不自崖于一揆;若令合而后乖,则释迦与尧、孔,发致不殊,断可知矣。是故自乖而求其合,则知理会之必同;自合而求其乖,则悟体极之多方。(29)这是说,佛教的神妙道理有两种情况,一种是先相合后乖离,一种是先乖离后相合。先合后乖,如诸佛如来就是。先乖后合的,如历代君王等就是。为什么这样说呢?据佛经上载,佛有种种神妙法术,能灵活变化,或变为灵仙转轮圣帝,或变为卿相,或变为国师,或变为有道之士,也就是说,世俗社会的诸王、君子,有的就是佛的变化身,这样由佛变现为帝王卿相等,叫作先合而后乖。或者也有的开创了大业,而功德未成就圆满,有的期待功成于身后,有的显应于当年,虽然有种种进退屈伸,但是最后都会归于成佛,这叫作先乖而后合。若就先乖而后合来说,成佛的途径多种多样,若就先合而后乖来说,释迦牟尼佛和唐尧、孔子都没有什么区别。可见先合后乖是佛化为各类统治者来到人间统理社会、教化众生,这可以说是政教相即的一种神秘形态。先乖后合是世间创大业有功德的人最终都和佛一样,将达到最高理想的涅pn@⑵境界,这可以说是政教先相离而后相合的特殊形态。
根据以上分析,慧远对政教关系的看法可以归纳为五点:第一是出家僧侣不问政治,不依附政治,独立修道。第二是在家信徒,既要修道又要遵守封建礼制,与政治保持相即不离的关系。第三是出家僧侣修道的最终结果有利于封建统治,这是深层意义上的政教相即关系。第四是神秘意义上的政教相即关系(先合后乖)。第五是政教由离而合的特殊形态(先乖后合)。从慧远关于政教关系的基调来看,他十分强调出家僧侣独立于政治,强调政教分离,同时又从多方面论证佛教与政治的一致性,肯定其相即不离的关系。从总体来看,佛教既独立于政治,又有益于政治的观点,是慧远政教关系思想的出发点和归宿点。
正文注释:
⑴⑵⑶⑷⑸⑹⑺(25)(26)(27)《弘明集》卷十二。
⑻⑼《比丘尼传》卷第一,《简静寺支妙音尼传》,《大正藏》第五十卷,第936页下。第937页下。
⑽释道恒《释驳论》引,见《弘明集》卷六。
⑾⒀《与八座论沙门敬事书》,《弘明集》卷十二。
⑿《老子二十五章》云:故道大、天大、地大、王亦大。域中有四大,而王居其一焉。王弼本、帛书甲乙本均如此说,傅弈本王为人,谓人亦大,联系下文帛书俱作人法地,王字似应为人字。
⒁见《老子二十五章》。
⒂⒄⒅⒆(21)(22)《答桓太尉书》,《弘明集》卷五。
⒃《沙门不敬王者论在家一》,《弘明集》卷五。
⒇俗,原作族。
(23)(24)(29)《沙门不敬王者论体极不兼应四》,《弘明集》卷五。
(28)《释道安传》,《高僧传》卷五。
